

看遍世事变幻 追求光明和乐
著名女记者浦熙修的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浦熙修(左一)与全家人合影。右起:父浦友梧、母黄庵岫、弟浦通修、姐浦洁修、妹浦安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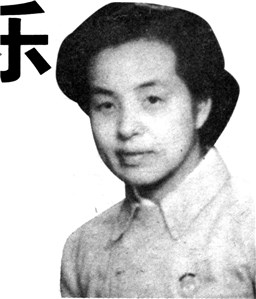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浦熙修是与会的新闻界代表。
每当儿女出世起名字,浦友梧老先生都要翻开那本发黄的《康熙字典》,洁修、熙修、安修、通修,二女儿名字中的“熙”字,释义光明与和乐。
浦氏家族在嘉定是望族,集中在真如、长征、南翔一带的浦家角。
浦友梧毕业于南京商业专科学堂,学的是会计,生下4个子女,生计有点勉强。1912年,浦友梧独自先到北平,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天天与算盘打交道。
1917年,浦家迁往北平,浦熙修7岁。
到了北平,浦熙修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顺利考进了初中和高中。哪知道,高中只读了一年,家里经济捉襟见肘,浦熙修无奈辍学。
1929年,浦熙修的同学们高中毕业考大学,她也试着报考了女师大。高中只读了一年理科,她却报考中文系,居然考上了。
在校期间,浦熙修与袁子英相识。袁子英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学教书。
1932年,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浦熙修与袁子英结婚。大学毕业后,浦熙修在私立志成中学教语文。年底,大女儿袁冬林出世。
在这前后,袁子英出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的经理。
神州国光社由陈铭枢投资所办。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反蒋,神州国光社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击。袁子英遭通缉,丢下妻儿匆匆逃到济南,后来经岳父浦友梧介绍,转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丈夫到了南京,父亲浦友梧也在南京,母亲已去世、大姐洁修在德国留学,浦熙修带着妹妹安修、弟弟通修以及女儿冬林,又教书又持家,在北平坚守着。1935年秋,浦熙修生下儿子袁士杰。
1936年,浦熙修带着孩子来到南京。她生性好强,引以为豪的就是17岁开始挣钱,还抚养弟弟妹妹,因此,不愿甘当家庭主妇。
一天,她看到某公司招聘职员的消息,就赶去应试。考试后,老板说:“这里不录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报社。
这次际遇,改变了她的人生。
在《新民报》,从发行到广告,浦熙修刚做了几个月,一次,有个纪念大会要采访,而记者都出去了,浦熙修匆忙前往“救场”。由此,“文笔流畅洗练”的她开始做记者,并逐渐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1938年,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新民报》迁往重庆。安修、通修在抗战初期先后奔赴延安。后来,浦安修与彭德怀在延安结婚。
在重庆的7年多时间,是浦熙修记者生涯里最辉煌的日子。
一身绿色旗袍,有时外加一件深色外套,手上夹一个黑色皮包,娟秀而庄重,一对酒窝又让她显得善良温柔。担任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奔波于山城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大路和小径,捕捉新闻。
丈夫袁子英也在政府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了个秘书的工作。家,就安在了重庆。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这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的真实写照。浦熙修以记者的责任与正义,写了一篇篇犀利的文章。
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进驻重庆,《新华日报》社、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浦熙修重要的信息来源。当时浦安修与彭德怀已结婚,周恩来、邓颖超夫妻便亲切地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浦二姐”的名气十分响亮。
1945年,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的一个名额本来是她的,但袁子英十分反感妻子热衷政治,只希望过安稳的日子,因而坚决反对她去延安,夫妻为此激烈争吵,浦熙修未能成行。
抗战结束,政局大变。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都是重大政治事件,浦熙修对这些新闻报道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政协会议开幕前一个多月,她就以一位职业记者的敏锐,策划了一组系列报道,精心选定了38位政协代表,每天发表一篇访谈。
民盟的宣传主委罗隆基是38位政协代表之一。绅士风度,典雅而又精致的生活方式,靠近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让罗隆基和浦熙修走到了一起。
罗隆基那年50岁。1913年,他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直接从小学考入清华,有“神童”之称。1919年“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与同学们一起放火烧了赵家楼。毕业后,罗隆基先后前往美、英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一说哲学博士)学位。他跟费正清教授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都是同学。
罗隆基1931年回国,与张君劢(嘉定人)等组建“再生社”,后改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日战争爆发后,罗隆基先后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教授,又任《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
罗隆基是一位西化的知识分子,浪漫且风度翩翩。他的发妻张舜琴是华侨、留英的同学,琴瑟不和,罗隆基给徐志摩、胡适的书信中谈到与妻分手的感觉:“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开6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
还没等到将来,罗隆基就在北平看上了与徐志摩离了婚的张幼仪(嘉定人),但张幼仪对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的追求毫无希望。
罗隆基在北平、天津又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美艳如花的王右家,不过没过多久又分手了。
罗隆基对女人体贴入微礼貌周到,殷勤献得自然自如又自在……这一切,加上博学和口才、风度与情调,便具有极大杀伤力——不管是少女还是少妇。
在他交往的女人中,保持关系10年之久的唯有浦熙修。饱经沧桑世事的磨砺,对社会、对人生见解的同感与默契,对政治,对民主、自由、进步的向往,让他们紧紧联联系在一起。
重庆作为陪都的历史结束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回南京。浦熙修也回到了南京的《新民报》社,8年前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小记”,如今已成“名记”。
在南京,浦熙修与罗隆基的感情急剧升温。
1947年,国民党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的要员大多离开南京。罗隆基离开的日子定在11月20日。19日晚上,罗隆基自然要约请心爱之人前来话别。当晚,浦熙修如约前往,被袁子英撞见,惹起风波。
浦熙修回忆说:“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的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了我的离婚。”
10天后,12月1日,在《新民报》老板邓季惺安排的一个茶会上,浦熙修与袁子英签字离婚,并在报上刊登离婚启事。
第二天,浦熙修即飞北平,在大姐浦洁修家里住了一个月。她写给罗隆基的信说:“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浦熙修后来这样解释。民盟被迫解散,罗隆基患肺病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浦熙修回南京,继续在《新民报》工作。
在南京时,浦熙修处处帮助共产党,无比热情,根本不惧怕任何政治风险。梅益说: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北平和平解放后,浦熙修本想立即经香港转去北平,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等我把治肺病的特效针打完,我们同走。”
形势发展得很快,南京解放了,浦熙修想,就在上海呆着迎接解放。
不料,当中却出了个小麻烦。5月10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国民党要劫持他们去台湾。浦熙修万分焦急,四处托人打探消息,还去过美国领事馆,设法营救。5月27上海解放,张澜、罗隆基终于获救。
1949年6月24日,浦熙修随张澜、罗隆基等人一同到达北平。
离开上海前,《文汇报》刚刚在上海复刊,徐铸成让钦本立送去了聘书,请浦熙修建立和主持《文汇报》北平办事处。她愉快地接受了新的聘任,期待到了北平可以跟罗隆基在一起。再说,大姐、妹妹也都在北平。
罗隆基住在乃兹胡同,这曾是北大前校长蒋孟麟的公馆,浦熙修特意在东单灯市西口朝阳胡同找房子租下,两人住处相距不过百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浦熙修是新闻界的代表。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就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呀!”主席这句话,让她感到无比兴奋,无比亲切,无比幸福。
从建国到1957年上半年,那段日子是美好的。旧社会的恶霸、地主、官僚、黑帮、娼妓一扫而光,社会治安良好,供应充足、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大大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发出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全国人民由衷敬佩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
然而,罗隆基却始终未将浦熙修明媒正娶迎进乃兹胡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彭德怀浦安修夫妇坚决反对。安修再三相劝:“罗隆基可以做政协委员,可以担任部长,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女婿!”二是正在上大学的一对儿女坚决反对。
浦熙修也证实了这种说法:“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他也无意与我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仔细分析,有些事情似乎不可言喻。
日久方知味,笃定下来识得君。罗隆基这段时间同时跟罗仪凤、浦熙修、杨薇来往。
倘若是真,会让人感到一身冰凉!
同居10年,浦熙修心里应该清楚罗隆基爱不爱她、又有哪些风流韵事,这种男人靠不靠得住,她没把握。
另一方面,浦熙修从做记者开始的那种追求进步、要求上进的意愿,也促使她要与这花心男人保持一定距离。
这段时间,浦熙修3次访朝,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回国后,又风尘仆仆,天山南北、黑河上下继续她的新闻事业,报道祖国建设的欣欣向荣。
时间捱到了1957年。
6月21日,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访问斯里兰卡回国,飞机降落昆明机场,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笑脸,而是那篇令人震惊的《彻底批判章罗同盟》的文章。
8月10日,政协文化俱乐部内批判罗隆基大会开始,浦熙修同罗隆基划清了界限的发言寒冷彻骨:“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她还交出了10年间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昔日口若悬河的罗隆基这时万口莫辩,无从发作。他只有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
其实,我们不懂她的心。
白色恐怖中,跟共产党暗中交往,她从未有过惧怕;特务的跟踪,在她看来,只是老鼠戏猫的游戏;下关惨案,她视死如归,用身体掩护雷洁琼;70多天国民党的大牢,她坐得坦然。以她的坚强,哪怕再来点辣椒水、老虎凳,也休想从她嘴里撬出一个字。而这次,却是一心向往的共产党的召唤。如果说党是太阳,那么浦熙修就是向日葵。对党,她一生都仰望渴求,甚至在遗言中还希望能够入党。党的话、组织的要求、领导的嘱咐,她从来没有马虎过!
可叹的是即便浦熙修与罗隆基划清了界限,最终自己却还是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共划了552877名右派,后来,只有5人未获平反,其中就有罗隆基。
1965年,罗隆基突发心脏病去世。夜里发病时,他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
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逝世,她得的是癌症。那年,她正好60岁。
他俩离开人世的情形惊人相似:孑然一身,没有任何亲人在侧。弥留之际,他们是否惦念着彼此胜似伉俪的情谊?以他俩一世的聪明和激情,是否冷静地思考过时代造成的创伤、叹息历史的诡异与人生的无奈?
浦熙修一生都在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与众多共产党的高官相识,不可谓不能干,不可谓不积极,不可谓贡献不大,全中国有数以千万的中共党员,唯独没有接受她的入党请求。在她看来,入党才叫光明。
浦熙修与前夫袁子英的感情一直不冷不热,与罗隆基相恋10年,最后却怒目翻脸,无和无乐。光明与和乐,在她一生中,可谓俱无所获。
风吹云散,浪卷波平,当我们回忆这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只希望《康熙字典》里那个“熙”字所含的光明与和乐,会普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